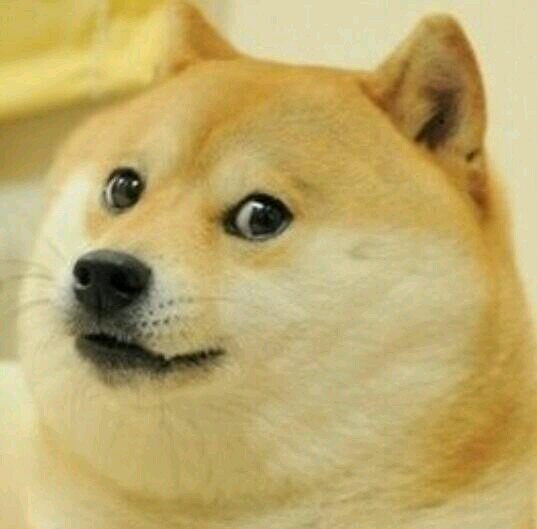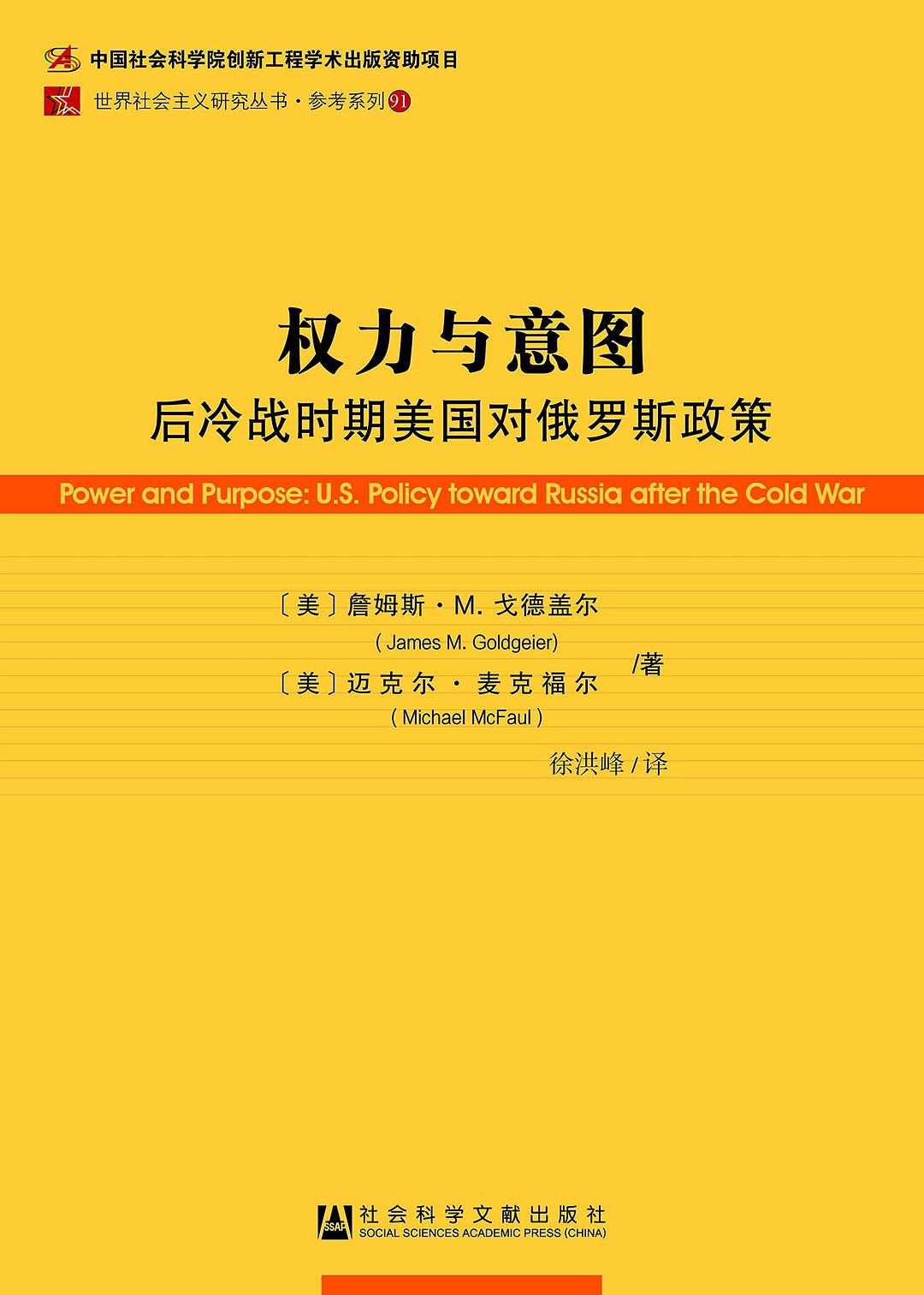权利的成本
权利的公共性
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和桑斯坦所著《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于权利所持的观点与态度。作者的观点,既批驳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即美国保守派——所宣称的“消极权利”,也不同于美国自由左派的立场,似乎只能将之称为自由中间派。然而,本文认为,无论持何种立场,真正对权利的分歧应该只有一个——对稀缺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方式。
一、权利的本质:公共资源保护的利益
哲学家以塞亚·伯林首创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由此,自然地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划分。所谓“消极权利”,即要求国家不必对自由权做任何的行为,一般认为其来源于启蒙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的表述。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霍布斯曾说:“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7页。]]而“积极权利”完全相反,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介入私人领域来保证权利。然而,《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这里的权利,是描述的(或称为实证的)权利,与自然权利或道德的权利有本质区别。书中将权利视为在有效的法律体系下用集体资源加以保护的利益。由此引出了作者的核心论点:权利是有成本的。在现实中,不存在未经过政府确定并加以保护就由私人所天生享有的权利。这是因为,如果权利的边界、内容、实施形式等得不到法律上的确定,公共资源也就无法对个人权利进行具体的保护。这意味着在此情境下每位公民都可能在无时无刻地被侵权,也可能无时无刻地实施了侵权。如此,个人就从不曾真正地享受权利,也就不曾拥有任何权利。即便是自由——某些语境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法律所确立和依赖公共资源提供的保护,那么个人的自由也无从谈起。耶林表示:“权利自身不外是一个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页。]]事实上,本文认为书中关于成本的观点可以看作脱胎于社会契约论。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就曾写道:“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这一切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80页。]]而权利是“法律的产物”也并非作者首创。洛克的描述为:“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36页。]]可见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是以政府的存在为前提,以积极的政府为保障的,而作者更是将其直接概括并总结为本书的副标题“自由依赖于税”。本段对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大量的引用,意在说明早在启蒙运动初期,人们(至少是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权利是有成本的,每一个人都向政府支付了保护权利的税。近代以来哪怕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保持一个最低存在程度和基本执行力的政府是必要的,否则他们最喜爱的自由市场将不复存在,书中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经济学不言自明地以一个积极的、可靠的刑事司法体制为存在的前提。因为实证的权利在中文语境中可以解释为“权利和利益”,所以权利(或权力)是极可能在个人主张权利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滥用的。只有权力才能对抗被滥用的权力。没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是不可能保护权利的,则权利只会停留在繁杂的法条之中而不被个人所真正地享有。然而在当今的美国,这个观点总是被某些人或派别刻意地淡化了。作者将权利的本质重新唤回到公众视野,使人们关注到权利对政府的依赖性而非单单是理想主义的崇高性,不仅仅是纠正了广泛传播的具有误导性的观点,还将对公民更好地实施权利和政府更高效地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权利的成本:深谋远虑的经济考量
既然权利是有成本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便由此产生:有限的公共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以保护权利。首先,税收的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法做出了关于“税”和“费”的区分。“税”是对整个社会征收的,“费”只向特定的受益者征收。近代德国法学家京特表示:“只有当单个的个体被定义为群体的必要因素时——只是因为他的必要性,他才拥有为能够满足他的义务所必须的条件。”[[[] 【德】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所以缴纳赋税在当今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民义务。这就回答了向谁收税的问题。但是,收多少税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古今中外,围绕着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屡见不鲜,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都是由此爆发,美国独立战争就是因为英国殖民者征收重税而直接导致的。可见,税的收取必须合理,既不能造成沉重的负担,又要保证政府有足够的执行力。这是个两难的处境。从政府角度来看,权利的预算成本已经是昂贵的。作者在书中列举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从联邦机关到各州机构为了保护权利花费甚巨,却仍然有大量的私人权利得不到很好地保护。但征税不能无限加重,如果政府为了尽善尽美地保护每一项权利而大幅度提高赋税,可能将取走公民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财产。如果公民贡献了所有的财产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无疑是荒唐的。权利的物质性不得不被仔细地考虑。其次,社会成本也被计入了权利的成本之中,正是如此,深谋远虑的经济考量是政府制订政策时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政府几乎是没有盈利能力的。本书作者将政府视为资源共同体,即一定程度上政府代表了公民组成的社会。而从长远来讲,对政府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扩大税基并减少未来可能的开支,这也是能促使整个社会获益。实现这一目的的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保护最重要的权利。权利已经是在当时政治和司法下价值很高的利益,最珍贵的权利更是如此。例如,财产权是公民最珍视的权利。正如孟子所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私有财产鼓励劳动、鼓励创造,能够激发每一个人的工作热情。这无疑会扩大政府的税基。而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人和稳定的社会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长远来看财产权得到保护更会减少政府打击犯罪的开支,并给整个社会带来巨额的财富。再比如,言论自由被美国人视为最“重要的宪法权利之一”,因为享有言论自由的公民不光可以反抗政府暴政,还可以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如此,从预算成本来看,政府只保护了一项权利,却间接地保护了其他权利而节省了大量社会成本。当然,正因为如此最重要的权利也往往是相对昂贵的。最后,以上文的分析为基础,公共资源合理的配置方式已经有了一些基本而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同的权利之间是有优先级的。权利的优先级取决于长远观点下进行的关于权利的成本的计算,尽管可能没人能给出详细的数据,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考虑了所有的预算成本和社会成本——包括对可扩大税基和未来可能减少的为保护权利的开支的计算——成本最低的权利将拥有最高的优先级,也应该是我们最先保护的权利。比如西方国家在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后所大力提倡并实施的福利权,既可以使个人更好地工作以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减少犯罪活动,由此减少了权利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要把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保证用来保护那些优先级最高的权利,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权利。
三、权利的交易:复杂的权衡与道德义务
然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充斥着难以预料的变化,有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情况:在权利之间作出权衡。毕竟,由于成本的存在,“权利是被有选择地保护着”。同时,权利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但有时很难明确冲突权利之间的优先级。这时法律必须做出权衡,甚至必须用权利制衡权利。虽然在拥有财产的多少并不相同的情况下,不平等将难以避免。为了避免社会底层为争取平等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社会上层不可避免地将权利进行交易。正如本书中所言:“用平等权交换社会合作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如何明智的福利设计是自由主义民主政治逃不脱的一部分。”社会效果从来都是法律所考虑的重点,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并自愿配合的社会制度将远远胜过通过暴力勉强维持的制度。一旦个人彼此自制、服从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清晰规则并且齐心协力,社会就会昌盛。但同时,权利和道德可能存在的冲突也暴露出来。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一个一直处于热点的话题。道德的滑坡是否与权利有关?或者义务是否与权利对立?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即“亚当·斯密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强调在道德上利他性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利己的《国富论》造成了亚当·斯密思想上的分裂和对立。但斯密自己认为:“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形成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怀有谨慎的美德。”[[[]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大概已经足够解释道德和逐利之间辩证的关系了。而本书中也列举了详实、令人信服的数据,同样显示了以福利权为代表的权利的扩大,并没有显著带来美国普通民众大规模放弃承担义务的现象产生。显然道德并没有崩溃,相反,法律是由道德期望塑造的,使权利具有法律执行力也将有益于公众相信这些权利具有良好的道德基础。耶林对此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利是个人的道德的生存条件,主张它是对个人道德的自我维护。”[[[]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页。]]这实在是与我们今天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当权衡权利和道德时,理想的状态是尽力使政治上可实施的权利与对他们而言的道德权利结合在一起。
结论:权利的公共性
通过本文的分析,权利完全依赖于公共资源的确定和保护,是维持社会这个资源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并最终产生对整个社会的效果。可见权利完全是公共的产物。对今天的人来说,从权利的成本来思考权利和政府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书在法律界乃至思想领域的影响将是广泛而具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