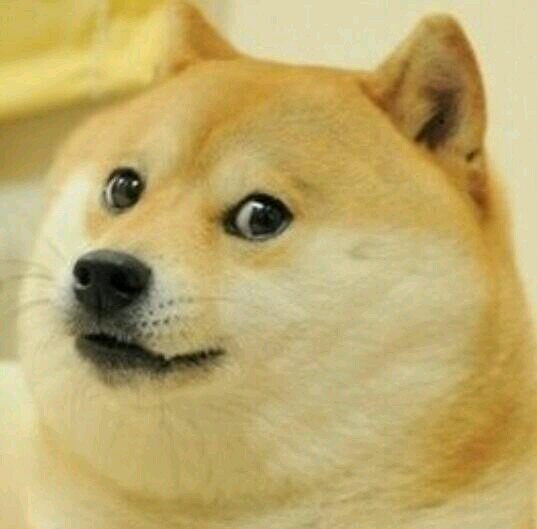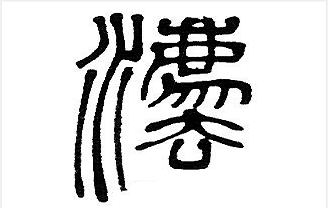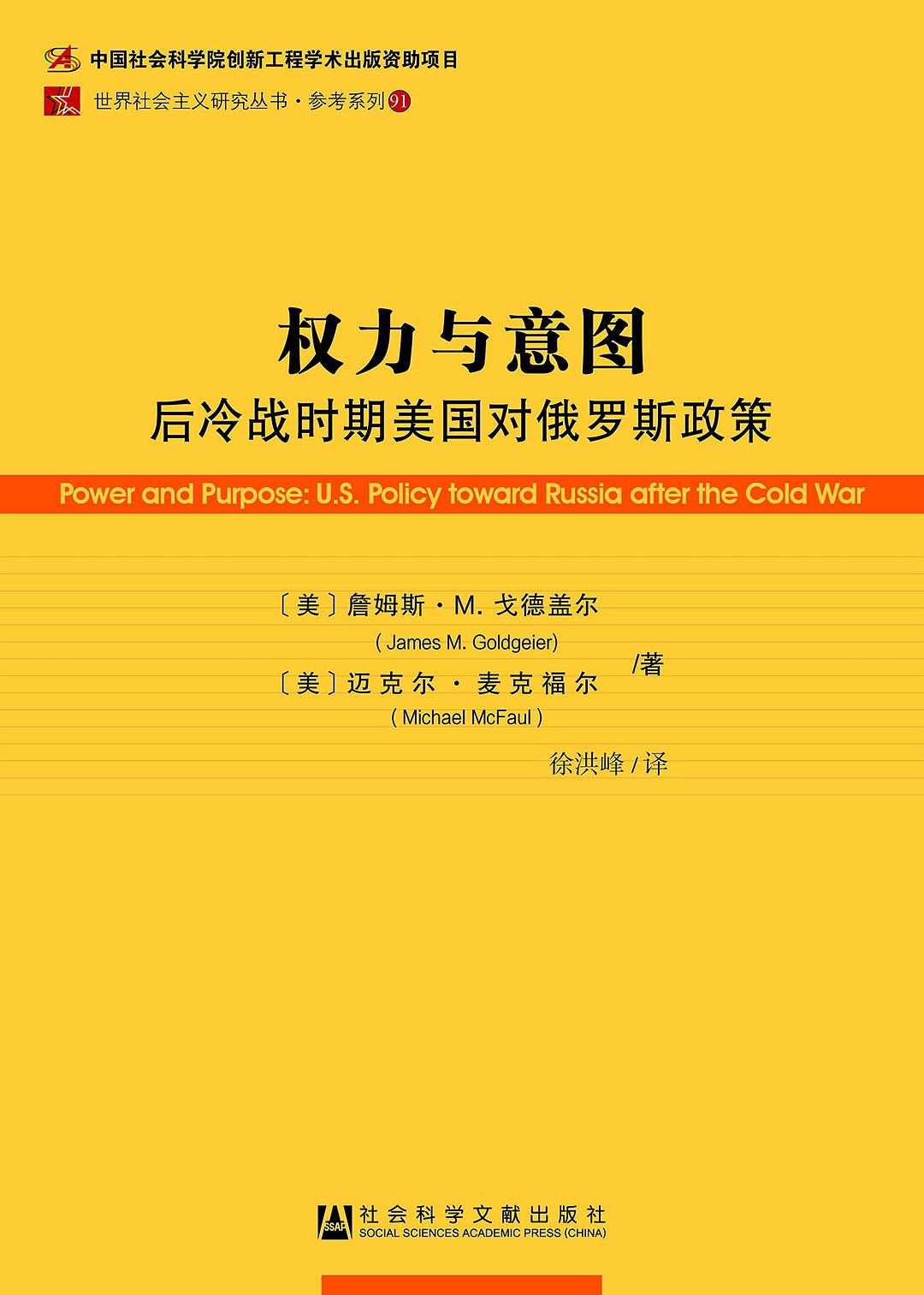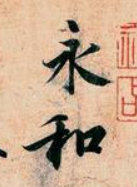唐律与传统法文化
《唐律与传统法文化》读书报告
通过阅读本书,我对唐律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法律的本质是反应并调节社会关系(矛盾)的工具。那么,由此可以阐述我的想法。
一、法与理的结合
相信每一个涉足过中国法制史这个领域的人,都会感受到“理”在法律中的重要性。那么,所谓理,其实在今天的解读有很多,如天理、义理、事理等。但唐律中的理,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天理、义理、情理。这三个理,其实影响着整个唐律的立法精神,也影响着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过程。书中第一篇即《唐律中的“理”》,这样的安排想必也是有深意的。
(一)唐律的法理基础
《唐律疏议》开篇即曰:“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这其实意在说明唐律的法理基础及其政治合法性。我们知道我国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儒家的法学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传统法文化。根据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学说,皇帝的合法地位来自于神的承认和授权,也就是“天”。那么,皇帝或者说朝廷所颁布的法律,应该是政治的延续,自然也要是“天”的体现。所以,法律要顺应天理。
既然认为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是,如果法律想有权威性,就不能朝令夕改。在这一点上,唐律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出自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唐律的法理基础是亘古不变的天理,不具有任何主观性,那么法律的稳定性也就得到了保障。天是不能质疑的,那么唐律也就是不能质疑的。这一点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既然认为天理是完美的、自然的,所以任何立法上的问题其实理论上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即最接近天理的。这样的理论会使得唐律的政治合法性在逻辑上自洽,并保留了法律技术上持续进步的空间。唐律的制定也确实是人们模仿自然、追求天理的一种体现。
(二)义理
唐律是以礼入法,即“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书中《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观点]礼,以及后来的礼教,就是义理。义理是由圣人根据天理的规律所确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外在的客观存在。因为圣人的智慧是后来人达不到的,所以义理也是不能质疑的。同时,圣人已死,那么义理也就是不变的了。这样,通过义理这个实际上唐律的第二个法源更进一步保证了唐律的权威与稳定。同时,义理成为法源,也是在可操作性上的一种补充。因为天理过于遥远,难以捉摸,但义理是人们可以接触到、学得懂的。那么,这其实也表现出唐律对人的一种期待: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圣人理想中的社会;法律希望每一个人都以圣人为标准对照自己。同时,义理其实给出了我认为的法律对社会最重要的作用:给人民一个判断是非的朴素的正义感。义理,规定了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等一切道德上的一般标准,这个功能其实是先于法律去实现而后才被法律所正式确定的。从这一步开始,法律开始参与构建社会秩序并规范人们的生活。
(三)真正的法律
我们常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可以执行。但其实,法律的生命更在于被人们信服。而,情理才是人民信服法律的最直接的原因。广义上说,每一条法律都可以被认为是情理立法化的结果。人民的广泛共识,才是法律真正的根基所在。所以在唐律中,强调考虑情理的重要性。合情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合法更重要的。情理,直接关联人们的生活,也就成为了调节社会矛盾的依据。
这样,对照“三才”理论,可以得到三个理的逻辑关系。即:
graph TB
天理 --- 天
情理 --- 人
义理 --- 地
subgraph
天理 --- 情理
情理 --- 义理
end
subgraph
天 --- 人
人 --- 地
end
当我们认为天是完美的,而义理可以理解为自然法,也是完美的,那么情理其实是一种修补和调和: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理论上那种理想的、完美的程度,所以由抽象入具体、从理论到实践,均由情理完成。所以只要法律合乎情理,我们认为这就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天理是天,是法律政治合法性的直接来源;义理是地,是外在的普遍道理,是衡量法律好坏、判决对错的标准;而情理,上,承于天;下,学于义,是立法的根本原则,也是真正被使用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法律。[ 书中《“守法”观念下的唐律文化》对“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从操作性上进行了论证]
我们也会看到,虽然我们认为天理、义理都是抽象的、客观的,但终究,解释权在当时的、也是真实的“人”手中。既然情理其实是由人来解释的,那么在面对理论问题时就具备了极大的可操作性,法律及其解释也就可以实施适度地变化。
二、唐律的司法实践
(一)确定性
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是稳定的。所以唐律选取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模式,通过礼教确立法律,整个国家的法律就是家族法。法律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并加以保护。虽然随着社会进步,这样的理念被批判,但是在当时至少给人一个对结果的预期,这是有助于稳定的。同时,在一个社会内的和平,表现为利益分配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权利主体之间相安无事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律在财产归属、遗产继承,甚至是人身依附关系上有着详细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其实都是由礼教所确定的等级秩序而来的。
(二)司法权力的限制
《唐律疏议·名例律》有如下内容:“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句话便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精髓。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所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体系严密的唐律,虽然严格限制了官员加重刑罚、罪刑擅断的权力,但是却并不严格限制行政官员减免刑罚、示仁爱以民的行为。这其实是儒家审刑慎罚观念的一种发展。
限制司法权力,在《“守法”观念下的唐律文化》一文中也有阐述。这篇文章认为,不得肆意修改法律、不突破法律的限制,其实是并非是对官员的限制,更多的是使皇帝不会因一时激愤而失信于天下,“守法”是皇帝取信于民的表现。这个观点恰恰印证了第一段关于唐律的法理逻辑的论证,即法律源于天道而印证于道德。所以,虽然我国古代仅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规劝皇帝,在制度上并没有对最高权力的限制,但其实皇帝也并不能为所欲为,任性的皇帝都是以失去天下为代价的。
(三)判决中的理
无论是在唐律中,还是在真正的司法判决中,都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即断案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条件。比如“故意”与“过失”,会极大影响断罪量刑。这显然是法律情理化、道德化的体现。同时,我们看到官员给出的判决理由更多侧重于说理,而不是引援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就是为调节社会矛盾而存在的,判决是给百姓听的,而不是给天地听的。如果判决不能取信于民,即使在逻辑上、在学理上说得通,也是不可取的。
三、一点思考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律的本质就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法制史领域学到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法律既然是工具,那么自然有不好用的时候,自然有要更换的时候。法律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如果执拗于去探究所谓学理、所谓理论,我想这只能陷入一种的误区。因为法律,更多的是一种经验[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万有引力定律放之四海皆准,但法律哪怕只是越过了国境线就不适用了。毕竟所谓客观真理,可能仅仅只是我们想象的产物,随着空间和时间的不同,那些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在变化。事实上早就有法学家对自然法进行了批判。[ 参见袁方:《法律实证主义者对自然法的批判及评析》]那么从社会共识而来的法律,自然也在变化。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萧条后的美国人支持罗斯福新政,美国最高法的大法官完全失去了民意基础,而法学界“被迫”开始迎合民意。[ 法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关注法律的实用功能,这一运动持续时间广,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这样研究出的法理、学理只能反映并适用于古代社会,于今时今日几乎没有借鉴的意义。毕竟法律是服务于现实,并且仅仅服务于现实的(很难理解法律会服务于历史或者其他的理论)。一个只属于某时刻的理论是不能成为经典并得到发扬的。为什么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等都是史学领域,而单单法制史属于法律领域?这种困境其实迫使很多法制史的研究者放弃以法为切入点,转向训诂、考据,逐渐向史学研究者靠拢。
但我认为,法学仍能成为一种角度。当我们对传统法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法律中,到底什么是不变的?其实有很多。首先,我认为是立法的精神。无论哪一时期、哪一国家的法律,总体来说都是希望并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人文的精神,其实是超越了法律技术本身得到不断传承的。以此为基础,我们的历史一脉相承,这种精神必定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关注最原始或者说最本源的法律的观念,其实是这一领域独有的优势所在。其实,既然法学服务于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定义、概念被修改、被补充或者被推广。随着时代的变化,那些被补充的、被推广过的内容,也就失去了现实价值。比如,法律的起源来自于复仇,那么,何不重新思考本源的法律?这样去研究法律史,在洗去铅华、去伪存真之后,传统法的研究应该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不正是所谓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吗?毕竟我们研究历史功利地说还是希望对现实有所帮助,那么这样去研究法制史,将对我们的未来的法律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